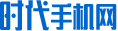在鲁迅文学院的日子拳
在鲁迅文学院的日子
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在鲁迅文学院的那段日子的记忆,恍若如梦,愈来愈淡了,愈来愈朦胧了,像隔着一片缥缈的出岫的烟岚,一片淡蓝色的暮霭 。
是一九九 O 年的初秋。
当我穿越了半个中国,像拜见圣地,走进了鲁院的大门时,映入瞳眸的,是那幢教学楼半面山墙上爬满的青藤。没有一丝风,蝉声嘹亮,午后静静的阳光下,那织锦一样繁密的青藤,翠微葱茏。而我的心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陷;一半是忐忑,一半是兴奋。我不知道在这里,能否醍醐灌顶,给自已红袖添香?
那时的我,青涩还不曾褪去,有着所有文学青年一样的梦想。我也深知,文学之路是是孤独的,孤单的,没有止境的,迢迢复迢迢,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凤毛麟角,而在塔底徘徊的,却如过江之鲫。所以我一直很谦卑,对谁都说自已是来学习的,低微到了尘埃,远远没有其他学员的张扬与豪气。在挂着很多中外文豪肖像的教室里,一位南方的学员望着镜框里不语的他们,不屑一顾地说:他们,也不过如此。我对他刮目相看,佩服极了,我想:能说出这样豪迈与大气的话的人,一定是翘楚,是才俊,才高八斗。许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在纸媒上读到过他的片言只语。我不知是他过于张狂,无处安置自已的灵魂,埋没了自己的才华,还是造化弄人?
同学的年龄大都良莠不齐,来自大江南北,携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经历,但都离家别舍,带着一丝淡淡的落漠与轻愁。晚上,情趣相投的,便聚在宿舍里,一瓶红星二锅头,两只卤鸭,随心随性,边吃边喝,山南海北地神聊,聊奇闻轶事,聊自己作品的得与失,也聊对远在天涯的家人的思念,不经意间,时间也就自眉梢发尖悄悄的滑落了。
讲课的老师,大都邀请文学大咖或校外中文系的教授。有那时写过《塔埔》《一地鸡毛》的刘震云,有汪曾祺老先生。刘震云比我大不了几岁,那时是《中国农民》社文艺副刊的副主任,上班就在鲁院的隔壁。他讲课,平铺直述,就像侃大山,说自已山一程水一程的经历,柴米油盐酱醋茶,娓娓道来,却很走心,很温暖,有着浓浓的人间烟火的气味,因而很受我们的欢迎。汪曾祺讲的是他的短篇小说《陈小手》课后,几位女同学围着她合影,小鸟依人地依在他的身边;坐在椅子上的他,不语,微微颔首而笑,带着南方男人的睿智,儒雅,淡定,从容。
与我同期的学员很多,有4十人,两个班,但也良莠不齐,后来有文学成就的,不多。新疆的赵光鸣,常常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年后担任过新疆的作协副主席;安徽的陈桂棣,是写报告文学的,曾获过茅盾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走出鲁院后写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担任过合肥市的作协主席。在鲁院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就很高,戴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桂冠,足见他们的作品巳有沉甸甸的份量。
那时,就听有人说,鲁院是中国文坛的黄铺军校”是培养文坛将才”的学府。不过,从鲁院确切走出了不少耳熟能详,星斗般熣燦的作家,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像蒋子龙,像王安忆,像张抗抗,像刘震云,像余华 。
那段时间,虽然身在皇城跟下,周末没课,我最爱去的地方,是中国美术馆,那里是绘画书法艺术的殿堂,有冲击视觉的华丽盛宴。由于对艺术院校的学生开放,免门票,我就持鲁院的学生证,一次次的去,在静静的展厅里,浓浓的艺术氛围里,近距离的静静地欣赏们的作品。有国画,有书法,有关山月的,徐悲鸿的,张大千的,黄胄的,也有赵朴初的,启功的 … 有一次,我还见到了出席剪彩仪式的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她满头华发,端庄慈和,仍掩盖不尽年轻时的风姿绰约与楚楚动人。
岁月匆匆,弹指间,告别鲁院已有二十多年了,有时,在梦里,还模糊显现着昔日同窗的音容笑貌。昔为同林鸟,今做分飞燕。我想,在夕阳西下的傍晚,灯火阑珊的夜晚,他们也如我,会忆起那段有梦也有浅愁的日子。
孩子咳嗽舌红苔薄黄吃什么灯盏细辛软胶囊怎么样
优卡丹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功效
- 上一篇:p患上不孕不育的原因具体是有什么p拳
- 下一篇:新春佳节与家人煮茶品茗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