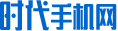藩国陈世旭文学温暖的家园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搬家,清理旧物,把刊载了自己有限且早已速朽过时文字的报刊尽数送去了该去的地方,留下的纸堆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1980年在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学习的教材和笔记。 教材是打字油印的,已经变硬发黄,但油墨的气息依旧暗香浮动。封面是一张单薄的普通白纸,上面是打字油印的 某某谈戏剧 、 某某谈《红楼梦》 等等,但那 某某 ,无一不是光耀史册的大师。 比小学生练习簿稍厚的笔记本是我当时咬咬牙特地新买的,廉价,但是方便携带和保存。家用拮据,花钱不能不精打细算。因为急于记录,字迹潦草,但其中透出的几十年前的日子却格外清晰。 1980年4月的一天, 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朝阳区左家庄的一个小院,前后两排平房,中间有通道穿过,通道尽头是课堂兼饭堂,外面是一片小小的核桃林,林子边上有一个大蹲坑的茅房,男女之间隔着一堵泥墙,动静了然。 对我来说,这个小院是圣殿。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才,开办了文学讲习所,办了几期,因为政治原因停了。 文革 结束,老作家们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回应,恢复的文讲所延续中断的学期为 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 。许多当时的文坛新人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 我由《十月》杂志的推荐,也有幸忝列其中。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挤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 文讲所分组的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吃饭,然后早早地走进还没有收拾完早饭痕迹的课堂,去前面第二排占了座位 从上海来的王安忆已经端坐在那里。我所以选第二排,是因为这里既靠前,又不太过分 我这样做已经够自私的了。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读书的机会,谁不想离老师近一点啊。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坐下之前,我找了块擦布把桌椅重新擦了一遍。这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至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她因此容忍了我的唐突。 我是爷爷的长孙。小时候我母亲跟我说,爷爷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怕我因为家贫失学。为此我父母先后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在初中毕业独自下乡谋生。之前的课外阅读,除了借看家境好的同学的小人书,就是放学路过报刊亭时拜读报纸副刊。农场8年,每天两头不见光,从城里带去的同学送的几本外国诗人的诗集在 文革 破四旧 时连夜烧了。再后来给借调到县镇10年,常读的就只有几本专为批判反革命用做 投枪和匕首 的鲁迅选本,此外就是各种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和政治学习材料。我读不懂,也没有读懂的志向。后来看到张贤亮在劳改苦难中精研马列、平反后成了驰名天下的大作家的光辉事迹,万分钦佩,深恨自己虚掷了大好光阴 其实以我的基因决定的智商,就算没虚掷也白搭。大作家哪里是只要读多了书就能做成的?古今中外,大作家固然都是学富五车,但学富五车就都是大作家吗?说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那也得是杜甫那样的文学天才。 光凭读书,未必就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年我应山东一家刊物约稿写王安忆的印象记,主要的篇幅讲了文讲所的生活。其中有一大段话,被文学评论家胡平先生在当年中国作协全委会上讲演时引用: 但在骨子里,我却是个有卖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的听课。因为懒,我自己是从不做日记、笔记的。而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这更使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做她的教师。我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告诉她这一段那一段 值得记 ,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记的认真,同时表现自己的高她一筹。但诗词我却背她不过。她晓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这是可以肯定的。 胡平先生引用这段话,目的是证明因为在文讲所认真学习,王安忆才有了后来的巨大成就。作为当时鲁迅文学院(文讲所是其前身)的负责人,他这样的论述是情理中事,是职责所在,也是理论家水准的应有表现。他引用的是我本人的文字,言之凿凿,不容否认。由这段文字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同桌的学生,因为听课的差异,导致了日后写作的霄壤之别。我自然是与好学生王安忆相对照的可笑的反面教材:浅薄无知,自作聪明,班门弄斧,因为不好好听课,所以后来在写作上了无成绩。对我的浅薄无知、写作上了无成绩,我是认可的,因为多年的事实摆在那里。但我在那段文字里描绘的我的上课情状却并非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刻意的演绎和夸张。那一大段自我调侃的文字,用意只在衬托突出王安忆认真诚恳的品质,事实上,打死我也不敢有那段文字里的张狂。而且上课的时候,我自己就是那个 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 的人。 文讲所的诸位大家,入学之前,对于我就像遥远天边的星星,仰之弥高。混迹在他们中间,我的自卑莫可名状。许多时候,我总是坐在院子角落的一块石头上独自发呆。我觉得孤单,有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纠结着还要不要继续赖下去。 作家王士美在后来的一篇回忆这段文讲所生活的文章里,很感叹地写到了我当时的落寞憔悴,怯于合群。我很清楚,在那个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不过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地卷在这潮流里,跟着得了便宜的一个小角色罢了。 因为没有先天的才情,又没有后天的家学,我从小就记住了大由吴哥航空公司MD八三型飞机执行人们说的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小学到初中的9年,我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做完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二天早早起来预习课程表上将学的功课,一直都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后来,家里无力供我升高中,继而接受高等教育,没能实现九泉下的爷爷的最大诺基亚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愿望,一直都是我父母和我自己心头最大的痛。而今有了这样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怎么可能掉以轻心? 文讲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散的时候似乎有些兵荒马乱。同寝室的北京青年作家瞿小伟好心好意地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挤公交车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苦读寒窗,我连故宫还没有去过。最终告别文讲所的那天,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信赖、可以求教的众多杰出人物的寂寞中去了。这寂寞由于一度短暂的不寂寞而更显难以忍受。 文讲所之后,许多同学的声名如日中天,一部部作品让文坛一阵阵激动不已。而我,尽管对待读书跟对待写作一样极为较真,但写作依旧极为平庸。然而,这并不证明,写作用不着较真读书,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文讲所带给我的读书习惯,即便是这种极为平庸的写作也许早就停止了。 文讲所将近半年的学习,时间不算太长,但对我一生的意义,却是决定性的。它使我懂得了文学的神圣,懂得了文学的不可亵渎,懂得了文学世界的广袤无边,懂得了文学世界中的自己的渺小无比,从此有了文化的自觉。正是在那之后,随着生活条件和写作条件的逐渐改善,我开始按照文讲所老师开列的读书清单,有目的地慢慢建立起相对有头绪的阅读,也使自己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半死不活、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得以支撑到今天。没有包括文讲所学习以及文坛朋友的多方关爱在内的种种帮助,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而今,重新抚摸文讲所这些廉价的、灰黄的、字迹潦草的笔记,重新抚摸似乎是倏尔消失的几十年前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文讲所的日子,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 我极为认同这句话:作家协会是文学温暖的家园。不说别的,仅仅是 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 ,就足以让我感激终生!
清远白癜风医院哪家好蚌埠男科医院兰州哪里的白癜风医院专业- 上一篇:藩国br深夜里孤独难眠
- 下一篇:藩国清朝最后三皇帝为何不能生育人品差到如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