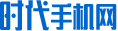藩国白花
清晨,吃了两个煮鸡蛋,喝了一杯牛奶,正想推开门去上班。回过头来,看了看还睡在床上的妻子,叫了声: 雅琴,快起来,该上班啦! 她只是动了一下身子,又呼呼的睡了。我转过身,开了门,骑上了自行车。
清晨的大街,几个行人。昨夜的一场大风雨,把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冲刷得斑而是更多依靠市场退出淘汰驳陆离,路上到处都是被雨水冲掉的块块碎纸片片,有白的、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被风吹得满地都是,墙上还残留着写有 砸烂狗头 、 永不翻身 、 打倒走资 的一些残纸碎片,让风吹得飞来飞去,纸片上残留的雨水,好象有人痛哭哭泣的眼泪,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湿了一大片黑色的柏油路面。
办公室里没有,我坐在椅子上,看到墙壁上挂着在大连演出时,全剧团人员在星海公园海边的合影。穿戴戏装的剧照都已经焚之一炬,唯独这张照片还是保存了下来。照片上,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女人叫李木子,也许是人多,怕挤出镜头,紧紧地靠着我,那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搭在我肩上,由于她是搞舞台美术的,照片上那姿势是那样的浪漫,那样的美,笑容是那样的甜,腮边两个酒窝是那样的深,眼睛大大的,照片人物太小,只是看不清那黑白分明的眼神。这张照片,雅琴生了好几天的气,但那是集体合影,她也无可奈何,照片继续挂着,只是我家的那张早就化成灰烬了。雅琴是演青衣的,她演出过我写的剧本,俩个人经人介绍,熟悉才二十多天,也没有经过恋爱阶段,她就嫁给了我。结婚快一个月了,不让我碰她一下,不是合衣而眠,就是用被子把捂个严不透风,要不就夹床被子到沙发上去独睡。为此,我请教过医生,大夫说:这是一种疾病,叫性冷淡,女人患这种病的比较多。给她吃了药,没有好转,又找了几个偏方,也都不见效果。我三十好几的人啦,碰到这样的女人,连个孩子都没有,这还象个家吗? 昨天夜里,我拉过她的手,柔声说; 雅琴,到我这儿来吧! 她冷冷地说: 就你是色鬼,看人家样板戏里的人物,哪个象你?杨子荣有媳妇吗?
那个年代,不光雅琴性冷淡,就是我们剧团,就是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性禁锢之中。公园里只有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小将用那生硬动作演出 永远忠于毛主席 ,谈恋爱的绝迹了,结婚的也少了,有那么几对办喜事也是骑自行车接新娘,亲朋好友,念几段毛主席,就算举行婚礼了。我考察过,就连生孩子的也少了,可能也都象雅琴一样,跟样板戏里的人物学习,患上性冷淡病了吧!也是的,几个有男女关系的流氓和走资派牛鬼蛇神一起戴着比他们身体还要高的纸糊的大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了,敲着铜锣,招摇过市,那些男女流氓的脖子上还要多挂几双破鞋。红卫兵小报还报道过某地枪毙过女流氓。
我们团造反派头头叫毕二虎,原来是把门收票的,大家都叫他二虎逼。因他批斗剧团团长最狠,把苗团长一头秀发剪掉,剃了个溜光,胸前挂了个五尺长的大牌子,扯着青筋暴露的脖子,嘶声喊叫: 打倒苗走资派,踩上八万双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就这样当上了造反派头头。他穿一身绿军装,还算合身,就那顶军帽,象大西瓜上扣个小酒盅,大小太不协调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走起路来,来回乱晃,他操着公哑嗓大声喊: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继续革命,今天继续揭发走资派的罪行,还是由张老编执笔,你这小子,写水笔字就是有两把刷子。
这时,雅琴慌慌张张地推门跑进来,演丑角的侯波,说了一句: 昨晚是不是和张老编演了一宿梁祝,演得精疲力尽,睡过了吧!
我倒上墨汁,拿起水笔。过来要我写苗团长这个问题,那个过来要我写苗团长那个罪行。小侯子凑过来,倒上了墨汁,坐在那儿半晌没吱声。我问: 你就说吧,就是词不达意,我也能编成好的。
对啦,对啦!有一年下乡演出,汽车跑了大半天也没到地方,大家都要睡着了,困得打盹。苗团长说,大家不要睡,我说个笑话,给大家提提神,说有一个老头子,去外地一个叫高朝村的地方办事。他怕坐过站,就问车上售票员: 同志,高朝到了没有? 女售票员说: 还没呢。 过了一会儿,老头子又问: 同志,高朝到了没有? 女售票员说: 你急,高潮到了我会叫的,我会叫的!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谁也没有睡意了。车终于停了,到演出的地方了,我随口说了句:高潮到了!你说,苗团长这是不是散布资本主义思想?
大家都写了,唯独李木子没有找我写大字报,搞舞美的嘛,字也写得漂亮。晚上,大家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大街上,没有行人,没有路灯,没有月光,一片漆黑,剧团里的人对这些用白纸、红纸、绿纸、黄纸写的大字报早就厌倦了,谁也不愿在这上面花费时间,粘贴完毕,都急忙地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上班,路过贴大字报的地方,有一张大字报吸引了很多眼球,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后边有个人还站在自行车货架上观看,我也挤过去。那是一幅画,画着一对男女从一栋黑房子里站出来,冲破了屋顶,直冲云霄。那女人梳一条辫子搭在那男人肩上,那男人戴幅眼镜,两个人的胸前各画一颗红心,那时带红心的图案很多,只是在红心的中央写一黄色的忠字,这两颗心上也有两个字,那字既象忠于的忠,也象衷情的衷,到底是忠于呢?还是衷情呢?谁也猜不透。旁边还写几个小字 冲破资本主义牢笼,奔向共产主义天堂! 落款是李木子。
这张漫画大字报在剧团里议论了好几天,二虎逼文化不高,他说: 不管打倒也好、冲破也罢,反对资本主义就是革命的大字报!
第二天,我问李木子说: 木子,你咋什么都敢画,什么都敢写呀? 她用深情地眼睛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 这不过是心里想说的话呀! 她又靠近我一步,反问我: 连声,难道这张画你都看不懂吗?还是剧团的大编剧呢! 说着嘻嘻地笑着走了。原来,远处雅琴正怒目盯着我们呢。
在一年以前,剧团的工作就是夜晚演出,白天排练。在彩排的舞台,演员穿着才子佳人或者帝王将相的服装一本正经地排练,锣鼓琴弦一件也不能少,苗团长坐在观众席的最前排,对台上的演员指指点点,台下还有几个演员对着台词。我和李木子一个编剧一个舞美,比演员可清闲多了,喝点茶水,看看报纸,有时还聊聊天。我对李木子也了解多了、熟识多了。她有个男朋友,中学的数学老师,二十五岁,他们结婚第三天被打成右派,失去工作,遣送到北大荒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刚听到释放回家的消息,又来了一场比反右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回家团聚的美梦破灭了。那时舞台布景都是画家画的,李木子也是一样,或站在高高的画凳上或坐在叉梯上。有一天下午,剧场里没有人,只有李木子站在叉梯上画布景,一不小心,梯子倒了,木子狠狠地摔了下来。大家赶到时,把她送到医院,办手续住院,由于时间晚了些,流血过多,需要输血,剧团的人只有我的血型和她匹配,我给她输了三百西西的血。这时又来了下乡演出任务,照看木子的任务,苗团长就交给了我。我白天在医院陪她,有晚上也不回家。木子的伤渐渐好转了。有一天我问她: 木子,为什么你画布景,总要画上几朵白花呢? 她笑了笑说: 我姓什么?
对嘛,果树园子开白花!我喜欢白花,她看上去有点,甚至有点凄凉,但她开的花,也一样炽热、一样清香。有一首韩愈的诗怎说的,大编剧?
我想了想,顺口说: 清寒莹骨肝胆醒,一生思虑无由邪。是的,白花,洁白,无暇,清淡,纯净。
一场秋雨一场凉,下了几场秋雨,天渐渐的凉了。二虎逼还是耀武扬威地比比划划,苗团长进了学习班,还是大字报、大字报,没完没了的瞎编,蒙天唬地的乱造。
省文化厅通知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我是作协成员,李木子是美协成员,我们俩自然都得到省城参加这个会了。
到沈阳开会的宾馆天已经黑了,会议登记处,两个小姑娘都打起了瞌睡。一位胖女孩看了看介绍信,对我们说: 好吧,你们就住五零八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男女两个人怎么能住一个房间呢?一想到批斗那些牛鬼蛇神、走资派、大流氓的场面,真是害怕。我正想问服务员。木子拿起钥匙,催我说: 快走呀!
我不知怎么上的楼梯,走到房间门口,还是不想进去,木子推了我一把,笑着说: 到家啦,进去吧!
那时宾馆客房很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的小桌子,两把椅子,暖瓶、茶杯,房间装饰只是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几条语录牌。
木子拿过介绍信,指着说: 你看,在是否党团员后面空了一个格,咱们都不是党团员,在空格上填上夫妻不就行了吗? 她亲了我一口: 这只是耍一个小伎俩而已!
木子脱掉外套就上了床,脱了一件又一件,直剩到了短裤和胸罩,她那两个高耸的戴着乳罩的的乳峰中间一道深深的 ,洁白嫩滑,好象有一股清泉,吸引着男人都想脱个精光,跳进去或潜水或娃泳,潇潇洒洒玩个痛快。她那肌肤是那样白滑光亮,象一个玉雕的美人,晶莹剔透,她笑迷迷地说: 脱呀,来吧!
我不顾一切地脱掉所有的衣裤,抱住了她。给好解开胸罩,扒下内裤。一股无名的快感穿透我的周身。结婚十七八年,我才真正尝到女人的滋味,竟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奇妙。我抚摸着亲吻着她那每一寸肌肤,莹洁光滑,柔嫩细腻。我们拥抱得那样紧,两块***融合到了一体,已经分不开谁是谁的身躯了,不管什么姿势,不管是猛烈的碰撞还是柔情的抚摸,木子都能配合得体贴入微,恰到好处。这时从窗外传来了象噪音一样的广播喇叭声,鬼哭狼嚎般地喊叫: 打倒大流氓! 大流氓不低头,就让他灭亡! 的口号声。这噪声,打乱了我们深情热吻和轻狂抚摸的情绪。
我打问服务员,她说: 今晚召开大流氓批斗大会,专门批斗那些乱搞男女关系的大流氓,去的人可多啦,一会儿我们也去,你们不去看看吗?
窗外的批斗大流氓口号声此起彼伏,床上两个相爱的男女紧紧拥抱。木子痛快的呻吟声,那样动听,那样感人,象百灵鸟唱歌一样的呻吟声,压过了黑压压窗外那乌七八糟的口号声。窗外乱哄哄的喊叫声越来越有气无力了,木子那呻吟声却象一首高亢的进军号,刺破黑沉沉夜空,即将迎来新一天的曙光。
可是,进到办公室一看,情况大变样了,那张在大连星海公园的合影,被摔在地上,满地都是碎玻璃碴子,那张照片丢在地上,一只穿军胶鞋的大脚踩上一个脚印子,全团穿军胶鞋的只有二虎逼。我拣起来,擦了擦,贴在胸前。苗团长走进屋,对我说: 快回家看看吧,劝劝雅琴,事情都过去了,坏人也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我愣愣地望着苗团长。她说: 你去学习,二虎逼趁你不在家,去了你家,以帮助学习毛泽东思想为由,对雅琴动手动脚,最后还奸污了她。雅琴哭得死去活来,好几天也没上班来啦。回去吧,好好劝劝她。
我没着急,心想,雅琴有性冷淡的疾病,别说你个二虎逼,就是吕洞宾来了她也无动于衷。武二虎拣不着啥便宜,随口说: 不忙,这回不向那二虎逼汇报,得向你正式地做思想汇报啦!
雅琴抱住了我,在我脸上深深的亲了一口,柔声柔气地说: 没说他,我说,我、我、我太想你啦!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句话,雅本期《超级战队》“铁肺挑战”让你看到“缺氧”了吗?琴是怕我知道那件事生气,还是真的性正常了呢?我故意气她说: 看人家戏剧里的人物,哪个象你?色鬼!
都象你象我,你看有祝英台就有梁山伯,有崔莺莺就有张生,有李双双就有孙喜旺,有刘巧儿就有赵柱儿......
后来,听有人讲,有性冷淡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同床,就能把病治好,谁知道这传言是真是假呢?反正我的雅琴好了。
这天清晨,雅琴对我说: 木子是个苦命的女人,不容易呀,这回走啦,准能奔上了一个温暖的窝,奔上个的家。咱们去火车站送送她吧!
唱响歌曲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们进了一家鲜花店,雅琴挑选了一棒白玫瑰,我愣愣地看着,雅琴又说: 白花好呀,纯洁,淡雅。
宣城白癜风治疗费用调经可以吃益母颗粒吗一岁半宝宝不爱吃饭怎么调理- 上一篇:藩国恒纪元监守者三百八十二章潘神的陨落
- 下一篇:藩国轻舞那年那月晒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