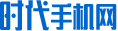藩国幽幽碧院
1.
梅雨绵绵下了几日,细小的柔丝薄薄飘洒一层,似而织,弱水洗后的青石板路越发温润。拈起裙角提着鞋子低头踩路,小心行踏,轻盈浅落,庭中寂静,母亲在燕子坞午睡,父亲在水墨轩读书,独我一人沐浴晴后阳光,徘徊院内寻迹访花踱步徜徉。
碧海青天阁前的夹竹桃愈发葱翠,簇簇荣成,花也繁多,一波未败一波又开,粉的素雅,红的妖艳,黄的新丽,散漫延枝,呈满慵懒之态。父亲曾说野蔷薇寂寞,美的姿态还在于它的利刺。将它种在墙里墙外偏僻的犄角旮旯,方增添其韵质,远远望去如云绚烂,比樱花还要烂漫,此式西方罗曼蒂克般的情致,点缀在东方古典的黛白瘦楼间,甄没了斑驳剥落的灰渍痕苔。
蛰伏隐居的夏蝉传出清越之音,鸣叫声浪折叠在盛荫间。母亲执扇已醒,隔窗呼唤我的乳名,筱姨打开坞子前扇花阁门,我回头正望见她莞尔笑颜,一脚迎出门槛,一脚仍在门内,招手示意我过去。丢下裙摆穿上鞋子,顿顿衣上珠滴,进入坞来。母亲困倦犹容,被蝉音吵醒,心中不免几分烦闷,待我问好,她便嘱咐我去剪几枝百合花来,再抱两盆栀子。母亲极其温婉,性如幽兰,平日里娴然悠静,倒把父亲显得活泼。我随母亲的性子,亦如孤稳,只好畸零,此二字还是父亲送我,说《红楼梦》里有一女子妙姑,乖僻痴张无人能比,她若早识我,也该认我做知已的。父亲儒生资质,说起话来惹人心痒,七岁我便读红楼,尚且识不全字,母亲颇有耐性搬出康熙字典,授我学知,即便读完,也是昏头恶脑,不知所言云云,但却梦中亦有所益。
筱姨陪我抱花,栀子淡淡的香味倾倒衣襟,她髻上钗饰叮当作佩,一路行来款款不已,十分美妙。手中的剪刀刚好盈握掌心,小心翼翼附颈剪掉,六枝系一束,筱姨笑说不要剪太多,反而辜负了它,我把剪刀交给奶妈,拿花与她向母亲复命。
母亲取出白玉插花瓶,又吩咐筱姨把栀子搬去父亲书房,正待筱姨要转身离去,我忙喊住她,栀子我要亲自送与父亲,让她稍等。把怀中百合抛给母亲,去天井边摇木桶汲水,这是家中单制的小桶,方便小丫头们便宜提水,并不是太重,每到夏日傍晚我便喜欢来此井边取水浸瓜。
筱姨汲水的功夫极漂亮的,每每引我羡慕,把绳子拎来手中左晃右摆,却只打半桶水上来,不如她一提便是清凉一桶。幸好半桶也足够装满花瓶,母亲不许在坞内装水,让小丫头抱来花瓶,在井边装水。水漫了一地,瓶口太小,不易注入,等到灌满,我的裙子也湿了大片。凉意掠过心头不禁一颤,捧着花瓶只得走碎步,进坞放到那张圆木朱漆大桌子上,母亲才过来插花。高低错落,横斜疏离,她插得一丝不苟,世间怎么会有如母亲这样的女子,让人猜不透她沉默的背后是怎样的心思,也猜不透她是怎样打发时间的无聊与荒芜。
父亲在读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嘴角一抹微笑。我进去父亲便撂下手中的书,喊道痴儿给为父倒茶,十足的清末遗老腔调,言罢爽朗而笑。把栀子花盆放在梨花木圆几上,又斟上清茶一杯捧与他,笑道爹爹用茶。我已换下湿了的长裙,穿上娟纱制的衣裤,父亲打趣道,洋人的东西尽管花哨,少女的长裙尚且素净,不过我家女儿养在深闺,还是古色古香一些更合妆宜。母亲说栀子清香,放在书香可以消夏,特意让我送来给父亲解解书中酸腐。听罢父亲起了兴致去观花,片刻只说花香集聚在一起太浓,把书香给冲散了,便把水墨轩所有的花阁门全部打开了。
明人计成有《园治》留世,父亲颇喜此书,当初来姑苏置办家业看了数十处房子都不满意,最后定在此处,一是因为此园颇有“夹巷借天,浮廊可度”给人以往复无尽之意,二是此院“小屋数橼委曲,究安门之当,理及精微”,大有“玄妙足以神通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的学问。三是因为“临溪越地,虚阁堪支”此居携天时地利人和宜人而修的缘故。原来的亭台楼阁已经破败,父亲请人一一加以修复改善,重新给各处房屋庭堂命名,改濒临水池而建天涯阁为碧海青天阁,仿拙政园的海棠春坞而建的燕子筑为燕子坞,只有水墨轩复原未变,冬临堂亦改为橙黄桔绿常。
母亲说园子是少些脂粉气,可惜书香气也不够,花香气也少些,名子被父亲改得也太不伦不类,父亲执起性子,冲撞起牛角尖,话也说得结巴,私家园林,我喜便可,又不要打开大门接八方来客,管那些个虚伪做什么。但是书香气却是没丢的,没过多久,一车车的黄旧书籍便从上海运来,那是父亲多年的存书。我家原住沪上的,为避战乱搬至祖籍,回到姑苏。
2.
苏州的夏日热浪冲天,葡萄架下却是凉满花荫,筱姨笑吟吟的在藤椅上放一把蒲扇,父亲会在午后在此歇息片刻,讲一讲孟子篇章。母亲只在燕子坞,时常忧伤的望着一庭花木惆怅,抬起手又放下,抚着胸口,母亲心中一定存在着隐痛,那种无法言说的无奈与荒凉,使她的背影显得单薄。父亲每次看母亲总在坞外,他犹豫着踱步,门窗关闭,夜色下一个在坞内,一个在坞外,都在无眠。转身,筱姨躲在银杏树后,盈满泪光。
三姑母带着表哥来住,伊对父亲冷淡,与母亲亲密,两人在燕子坞喁喁私语,说些出阁的女儿家的赶快去找到他吧。通过徐霞客的指点话,这话也该老了些,因为三姑母和母亲早为了这份爱情已不是小妇人,年过半百,紧随的纯真不足一丝,余下的全是端庄。表哥丢下包裹,跑来父亲书房,奶妈收拾行李准备房间,三姑妈是要到中秋才离去的。
“筱君她来这里有十多个年头了吧!”三姑妈看着那一点素色的衣衫在井边走动,拿褶子扇挡住了头,一抹流苏倾泻到眼角,黄灿灿的耀眼。
“二十年。”母亲喝茶,头也不抬,指间停顿,神情也颓委。
“她与五哥的事,总是个结,你还容得下她,真是贤惠。”偏偏头,向母亲笑,有些狡黠。
“兰儿在,不要提这些不愉快,说说吧,你跟姑爷怎么样?”母亲放下茶杯,恢复了以往。略微看看我,温婉的慈爱。眼角收住尾光,一梢阴郁随之散去。我走去窗前,伏几上支头,长发披散下来,看那一波碧池,母亲与三姑母的话还很长,要我作陪,她们做长辈的喜欢有小辈在跟前承欢,而且二女不凡,亦不会道人家长琐碎不堪,我很乐于听她们畅谈一二,仿佛智慧潜藏在那些漫不经心的话语中。
“守着父母留给我的嫁妆,管着儿子不要成他那样,也管不了那些纷扰,有一次他想着把几房姨太太遣散了,一来好留着钱财,二来大概也是老了,岁月不饶人,不想那么一味的胡闹下去,看他的身子竟是一年不如一年。”三姑妈摆弄着褶扇不急不慢,徐徐吐言。
“早知荒唐,何必当初闹成那个样子!”母亲接道。
“那个老房子我住了数十年,眼看着儿子也熬大了,突然间特别想离开,它就是一个牢笼,套牢了我的青春和一生。”三姑妈稍稍激动,这是她一生的遗憾。
“莫讲这些,你已经走出来了呀!新的房子住着还习惯吧!”母亲劝慰她。
“新房子还好,我倒不想要那种新建造的洋人式的楼房,冰冰凉凉的没有人气味,除去冷的墙和富丽的装潢,只有空的壳子。这点倒随咱们老太太,恋旧。”三姑妈道。
“旭峰今年小十八了吧,该娶亲了。”母亲道。
“旭峰长兰儿两岁,虚岁十九,我倒不急着要他娶亲,看他读书还好,现在时兴流洋,或许他想走这条路也未可知,看他也没有想娶亲这层意思,趁年轻,乐得放他几年自由。”三姑妈道。
“那孩子倒不是个会胡闹的人,一点也不随他那风流的爹,你也该宽慰。”母亲道。
“兰儿呢,你有什么打算?莫说咱们家还养得起,就是养不起也不要她随便的把人嫁了,这是一辈子的幸福,看看你我二人便知道了。”姑妈道。
“随她吧,现在还读书,守在我身旁,倒安静。”母亲道。
天色渐渐的暗淡下来,黑得真快,想起学校的铁栅门,有一小片洋红色砖的小屋子,里面住着烧热水的单身茶房,清瘦的面容,洁净的衣衫,那神韵很像配昆曲拉二胡的乐师。此刻十分想念他,大概因为天边的那朵红云,像他屋里那摊红色的桌椅。
晚饭摆上来,鸡鸭鱼肉皮蛋粥,青菜豆腐玉米羹,荤素搭配得一桌秀色可餐,母亲只有一年的这个时候才与父亲同桌用餐,就连过年也不例外的叫人送到她房内。筱姨站立一边,母亲让奶妈搬个凳子加在三姑妈下首,三姑妈微笑,筱姨便坐下一起吃饭。
大家相互问好,特别是三姑妈与父亲,生疏客气,表哥敬着父亲酒,三姑妈与母亲边吃边谈。那锅鸡汤厚厚的一层浮油,三姑妈嫌腻,舀了舀勺子又抽出来,母亲便嘱咐奶妈换新调羹给三姑妈,一会有清淡的酸皮汤。
三姑妈是我家最重要的客人,母亲不与旁的人有过多的往来,三姑妈是个例外,特别投缘似的,从三姑妈做姑娘时起,便常到嫂嫂房里来计较秘密,有一个时期我还小,父亲见她们也要吃醋嫉妒的,那时父亲和母亲的感情真的很好。情投意合,才子佳人,相会于月色荷塘,淡诗论道,如今再也难见母亲当年的风韵,她由于悲伤,渐渐的收住了,满腹的才华,也随风隐没在平静中。
三姑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总是扳起我的下巴,捏着我的鼻翼说越来越有嫂嫂的清秀了。只是我太腼腆,不大热心那些她笼络的事情,性格慵懒,没有母亲勤谨。你真该把所有的都传授给她的,陶养性情,这对她也是一种福分,不至于孤独寂寞。那么长的人生日子,若是没有点寄托,该要怎么熬过!三姑妈每每嗔念我,总不住的对母亲这样说,她所说的传授是母亲读书的气节。
也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
.
筱姨看到父亲总是欢喜的,接过他手中的书,递毛巾过来,想想奶妈真是辛苦,伺候了我长大,又要伺候父亲起居。父亲不常让筱姨过来,中间那点缘故,在三姑妈第十九次居住的时候,我已猜测得八分,由奶妈证实,事情原真是那样:筱姨是母亲收留的孤弱女子,母亲待她极好,像亲生姐妹,三姑妈亦曾埋怨过她们的情份。筱姨却在日后的时光中暗恋上父亲,背着母亲与父亲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母亲知晓的那一刻泪如雨下,可是母亲亦明白,心不在,人也徒留,尽管父亲的心依然还在母亲那里,可是却伤母亲至极,她灰心到放手,也懒怠着吵闹。
真不知道这种畸形的关系是怎样维护在静默之下,这全归功于母亲与筱姨,她们俩客气相对只字不提,各自安份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筱姨顿悟,但是她对父亲倒没有死心,三姑妈说她的心也是寒的,不是无伤的,只是那伤只适合自怜,不能博取别人同情。三姑妈向来是这个样子,说话在情在理也能刻薄三分。
上海的房子没有苏州的大,也没有院子。我与筱姨住楼上,奶妈和父亲母亲住楼下,但二人已分居,不在一起。拐角的房子另住些小丫头们。三姑妈嫁到苏州不肯去上海,那几年与母亲只有书信来往,邮差骑着大洋车,甩打着铃声,背着帆布邮包,每每母亲听到便亲自下楼取信。她收着信不看,等到每月十五的那天晚上洗过澡之后,穿着睡袍,趿着拖鞋走到阳台上,攀附在栏杆上,一手拨开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抬眉笑对那弯明月,手里拈着刚刚在浴室读完的信。我坐在沙发等她,远远的只有背影,波浪型的头发,很摩登的三十多岁少妇的身子,母亲有个阶段打扮得像个出洋的妇人,受五四时期新运动解放的影响。
过了四十岁她又恢复到中国传统的妆扮,从服装到发式,鞋子配饰,手链也换成了翡翠镯子。三姑妈送过她一只笼烟型淡墨的镯子,配素色竹布旗袍很合适,她收了戴着一直没褪过,其它的倒全部丢弃在一边。我玩着那只漆木的匣子,里面一堆的金玉辉煌,奶妈笑说那是将来我的嫁妆,要我小心,别打了它们,损失可就大了。
在上海的日子,每月十五晚上,母亲会陪我入睡,我抱着她雪白的脖颈,想着快快长大,不用每天闷在家里由奶妈掌管。等到真正的长大了,却又不想出门,任由奶妈啰嗦,爱极了那声长里短的唠叨。我骨子里是个怪人。来苏州后,母亲便扔下了那习惯,理由是我长大了,要抱也可以抱布娃娃,不必再抱着娘不放手了,该留给些女儿家的小心思给我。算算旧历,那年我正好十岁。
三姑妈来后,筱姨更需远着父亲,我不禁替她委屈,她很畏惧三姑妈。关于母亲与她,三姑妈说当事人要自己面对,也不许我对她不敬。其实我倒没什么对她有怨恨的,她待我再好,也始终隔着一层,那种没有热情的温开水似的相处,漠然的关心和问候,会有一切正常的心绪变化,却落不到心里的认可她。她很悲哀,我常想,连三姑妈与我都怜悯的人,再华丽也只不过是个空架子,经不住风雨的交替,她会枯萎死去。我们还不忍看一个女子伤心,所以父亲的处境只能尴尬。
第三个夏日,表哥远去了日本,三姑妈一下子老了起来,常常神经质的疑问旭峰哪里去了,思儿过度,人便憔悴。父亲把她接了来,与母亲作伴。我离开苏州回到上海美院,开始我的油画学习。于家中的消息,便生疏了,父亲与母亲会各自来信,告诉我各自的离索,我很心痛他们同一屋檐下的咫尺天涯。
筱姨在一个烈日里发痴,蓬头垢面,叫嚷不停,那恶疾来得突然,父亲措手不及,母亲回避,三姑妈看着家中乱作一团,与奶妈在厅外相对而坐。
大夫根本治不了筱姨的病痛,只说是发疯,可能是酷暑攻心,一时痰多迷了心窍,再有就是心中有什么隐秘,压抑得太久,此时爆发。隐秘?父亲不知,三姑妈进来冷笑,奶妈叹息。筱姨跌下床来,抱住父亲的腿脚乞求原谅,父亲拉她起来,她又跑去跪到奶妈脚下,父亲气急大叫。
筱姨真的疯了,拖拖拉拉挨到第五日便死去了。
筱姨的死去,也把那个秘密带了出来,父亲如五雷轰顶,一夜青丝生白发,浊泪盈框。
在那个黄昏,夕阳灿烂无比的时候,我收到了三姑妈的信,信中嘱咐我不许忧伤,原因那都是过往的事情了,也该是要我知道的时候了。
母亲临盆而生的是一对双生女儿,我是其中一个,上面的那个该是我的姐姐。筱姨因妒意故意将姐姐失手摔死,当她正要下手也送我入黄泉的时候,奶妈端水进来,吓得尖叫,诺大的屋子里,只有她与奶妈,床上躺着昏迷的母亲,她恶毒的用计支开了一切人。三姑妈原是来贺母亲,悄悄的一人跑来产房,未进门便听到奶妈尖叫,急忙进来时正看到筱姨高举起我的一暮,地上的姐姐已经断气,奶妈抱着呼唤不已。三姑妈从呆立的筱姨手中夺下了我……
三姑妈说世上最爱父亲的人是母亲,所以隐瞒了筱姨恶毒的一面,并容忍了她。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对她十分迷恋,母亲生育后筋疲力尽,已不想计较太多,她要为存活的女儿积福。
上了年纪的筱姨越发的内疚,三姑妈的凌厉的眼神像催命的债主,她终于自己折磨到极限疯了。死去了,还可以解脱,而父亲,一直不知,这突然而来的打击,更让他难以承受……
那院中的花儿开了又谢,凄凉的故事,便湮灭在纷纭的花堆里……
共 5619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院中的花儿开了又谢,凄凉的故事,便湮灭在纷纭的花堆里……幽幽碧院,爱别离苦。惊心动魄的故事,皆在无声无息的时光里开演又落幕。小说文笔细腻,回味无穷。【:上官竹】【江山部?精品推荐】
1楼文友: 10:00:07 很有内涵的作品,余音袅袅,耐品耐读。 联系:
邯郸白癜病医院南充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先声药业研发- 上一篇:藩国守住诚若
- 下一篇:藩国说起中国悬疑小说作家